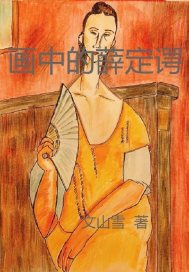黑狗干正忙着收拾餐台和火锅残汤,其他楼面上的人也准备收工。他盘算着待会跟老板鹰哥谈一下,拿上一个月的假,再借两个月的薪水,回西贡去看看父母。来仰光十几年了,只回去过五六次。有时候是有时间,没钱;有时候是有钱,却又没机会。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呀!回去一次也得花不少钱,亲戚朋友那儿都得有个交代吧?现在西贡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,这里有的东西越南什么没有!买东西回去送人,可真是件麻烦事儿,送小了,人家还看不上,送大了,自己又送不起,还真是的,要不送他们几辆车好不好?!
他正胡思乱想着,餐馆的门动了一下,走进来一个人。他头都不抬地道:“今日收工了,哞野食了(没东西吃了)!”
“我吾食野,我系揾鹰哥(我不是来吃东西的,我找鹰哥)。”声音挺熟。黑狗干抬起头一看,心里突了一下。这不是那个香港差佬古si
么?怎么这回凌晨两三点来宵夜来了?他马上想起牟子宽他们,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吧?他手指了指后面道:“哇,系你啊!梗夜出来宵夜咩?好耐哞见噢!柜系入边(哇,是你啊!这么晚出来宵夜啊?好久没见你来啊。他在里面。)。”。
黑狗干看着古si
的背影,心里突突地跳着。他不知道该不该赶快离开这里,如果现在就走,万一是有事,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?先不急啊,等等看。他想起牟子宽的手提电话,赶忙拨了一个,没人接听。再拨,还是没人听。黑狗干的额头开始出汗了。
正忙乱间,背上突然被人拍了一下,接着肩膀被人搂住了。他回头一看,就见古si
笑嘻嘻地看着他。“狗仔,打电话卑边个啊?女朋友?嘿嘿!来,我有点事想同你倾下。(我有事想跟你聊聊)”。黑狗干心想不妙,可是身不由己地给古si
拽着走了出去。走到门外,就见一个高高瘦瘦的鬼佬靠着墙在那儿抽着烟,眼睛瞄着他,那眼神跟头野狼似的。
“狗仔,里排力度吾系好太平噢!有人系力度骑梗木驴噢。你有哞料爆一下卑我啊?(最近这里不太平啊,有人在这里偷车,你有没有什么线索讲给我听啊?)”古si
仍旧笑嘻嘻地问道。
“吾系哇?大佬!我都不系好明你讲梗咩噢!(不是吧,老大!我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)”黑狗干心一沉,心想,完了!但是脸上仍然努力装着没事的样子。
“喂,细佬!我同你老细查过,次次有事,次次都系你当班。你依家老老实实同我合作,有么事我会悌住你格。(喂,小兄弟!我已经跟你老板查过了,每次出事都是你当的班。你现在最好跟我好好合作,有什么事情我都会照顾你的。)”
“大佬,我真系吾明你讲咩噢!我依家仲要手工返屋企,哞时间同你倾了。(老大,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!我现在要收工回家了,没时间跟你聊了。)”黑狗干转身就要走。
“企住!哇,衰仔!我依家系卑面你,你仲讲梗大话!(站住!好啊,小子,我给你面子,你还想骗我!)”
“你当差吾可以无端端阻住我做野格吗!讲话要讲证据,这里系法制社会噢!”黑狗干心知这次是大大的不妙了,只想赶快脱身。
“丢!企好!我依家怀疑你藏毒,哞郁!”古si
一把把土狗推到墙边,让他面对墙壁,岔开两腿,然后从上往下地搜身。摸到黑狗干的裤兜的时候,突然手一动,然后从裤兜里拿出一包小塑料袋,里面装着白色的粉末,放到土狗的眼前。“嘿嘿,锑下里个系咩啊?你今次死梗喽!(看看这是什么,你这回可是死定了!)”
黑狗干一看,犹如五雷轰顶。“你这是陷害我!”他顾不上再说东南亚广东话了,以前也听说香港差佬办差很贼,怎么这次自己就这么不当心呢!
古si
二话不说,一拳捣在黑狗干的腰眼上。“丢你个北佬!仲敢硬颈!走,跟我返差馆!(X你个大陆仔!还敢犟头倔脑,走,跟我回警局去!)”
黑狗干瘫在地上捂着腰,疼得大汗淋淋。他喘着气道:“大佬,大家都系唐人,做咩梗样对我啊!(老大,大家都是华人,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)”
“丢你老母!边个同你系唐人!我系香港人,你哞搞错了!(X你老妈!谁同你是华人啊,我是香港人)”古si
最恨的就是别人跟他用“华人”来套瓷儿,不由分说又是一脚。
颂亚眯着眼看着这一幕,心里就觉得象吃了只苍蝇一样反胃。狗娘养的!这样的华人他以前见过不少,香港,新加坡都有不少。虽然每次碰上这种人,他的优越感愈加地旺盛,但心里面却极端地蔑视这样的家伙。Thisisamazi
g,is
’tit?The
e’
ealwayssomeChi
eset
yi
gsoha
d
ottobeaChi
ese.让他这么对泰国人,就算对方是罪犯,他也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。ButthisisthemosteffectivewaytodealwithChi
ese,Chi
esea
ejustlikethat.他想到这里,摇了摇头。
古si
一把拖起黑狗干就往外面停车场上的车里拽。神志不清的黑狗干被一个花盆撞了一下脑袋,突然清醒了过来,他猛地一拉古si
的腿,把他绊倒在地。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掉在地上,土狗也不管三七二十一,捡起来转身就跑。
颂亚一惊,扔掉香烟就追。古si
爬起来,喊道:“企住!哞走!你走吾仂了!(站住,不许跑!你走不掉了!)”
黑狗干拼命地跑,他想起手里的东西,边跑边举到眼前看了一眼,然后转身就想扔掉。
颂亚在后面追着,看见前面在停车场另一头角落里警戒的那个手下也围了过去。他喊道:“Police,F
eeze!Stop
ightthe
e!”突然,他看见黑狗干转了个身,手里拿着个黑乎乎的东西,心里一惊,本能地拔出手枪。还没等他想好该怎么办的时候,就听见“砰”地一声枪响,前面的黑狗干踉跄了一下,往前软软地倒了下去。娘的!他气得跺了下脚。赶忙跑过去看,那个手下手里拿着枪,蹲在土狗身边,手里拿着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发愣,抬起头看了看颂亚:“oh
o,it'sacellpho
e!”
古si
也跑了过来,看着侧卧在地上的黑狗干。就见胸前那个被弹头撕开的那个大洞咕咕地流着血,嘴里鼻子里都在冒着血泡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拼命睁着眼,仿佛知道一旦闭上眼就永远都睁不开了。腿脚抽搐似的蹬着,但是连空气他也蹬不动。
颂亚看着黑狗干,摇了摇头,道:“He’sgo
e!Welostitagai
.”眼看着黑狗干的气息越来越弱,颂亚回头喊道,叫辆救护车来!然而一切都已为时已晚,黑狗干的动作最后停了下来。眼睛却仍然睁着,一动不动地看着古si
。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香港佬突然浑身发冷,猛地打了个寒颤,急忙转过身去,再也不敢看下去了。
牟子宽一醒过来,就闻到一股浓浓的咖啡香。他睁开眼,看见阿卡蹲在地上往杯子里倒着咖啡,柳天云捧着收音机,音量压得很低,正在听新闻广播。他刚要开口说话,手机响了起来。他抓起手机一看,是三眼。
“喂,做咩啊?梗早就打电话过来!”
“宽哥,黑狗衰左了!(黑狗干死了!)”
“啊?!发生咩事啊?”牟子宽大吃一惊,坐了起来。阿卡和柳天云都放下手里的东西看着牟子宽。
“今朝火锅店收工果阵时,果个香港佬带住两个泰国佬去揾柜。吾知搞成点,狗仔无端端卑一枪打死左。厨房的帮工话我,果个香港佬几恶,柜地在入边都听到柜系出边打狗仔哦!(凌晨火锅店收工的时候香港佬带着两个泰国佬去找他,不知道怎么搞的,狗仔无端端给一枪打死了。厨房里做的那个帮工对我说,那个香港佬好凶啊,他们在饭店里面都听得到他在外面打狗仔。)”
牟子宽想起黑狗干那张年轻的笑脸,眼泪不由得掉了下来。他电话里对三眼道:“你过来先。”
阿卡和柳天云不知所措地看着牟子宽。牟子宽抬起头,轻轻道:“黑狗干死了。”他看着阿卡道:“兄弟,我看得赶快把东西搞出去了。你查查最近有没有船来仰光的?”
阿卡想了一下,道:“我看看是谁的船。要是是我以前海大的同学,一定没有问题。唉,黑哥!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