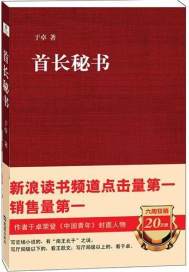1
李汉一正在跟温朴通话。
李汉一选择这个时候跟温朴谈担保是经过周密考虑的。自从温朴把担保的事掖给他,他就一直没再跟温朴提过这件事,他是在等生米做成熟饭后再跟温朴联系。现在是火候了,他先是对温朴讲了电力安装公司账号被封的前一天,他迫不得已找了袁局长,请他到一个姓许的行长那里通融通融。
李汉一平静地说,我想袁局长,肯定是没少使劲。没谈下来,也许是事情太复杂吧!
温朴听出他话里有话。李汉一现在把袁坤扯到担保这件事上,说明他这些天里借担保之事,没少打袁坤的主意。再就是当初自己暗示过他,担保这件事贴公沾私,不便外漏,李汉一难道会不明白其中的意思?现在看来他不但不遵守游戏规则,还一步迈到了袁坤那里,这一切的意外只能说明他这个人说话办事会找借口,会看火候,还会周旋。
温朴不软不硬地说,哎呀李局长,没想到这点事,给你找了这么多麻烦,不好意思。
李汉一说,哪里哪里,温秘书,这你就见外了。不过你不必担心温秘书,这件事虽说出了意外,但我会想办法妥善处理的,想必不会闹得沸沸扬扬。
温朴想,李汉一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,也就没必要再往下谈了,笑笑说,那就让李局长费心了,有新情况,咱们再沟通。这几天苏部长安排了不少事,不然我就过去看看了。
李汉一说,温秘书,担保这点事,你就不必挂在心上了。
温朴又客气了几句,然后挂机。
2
袁坤一直在办公室坐到天擦黑,才让司机把他送回家。
下午袁坤跟许行长通话后不久,就接到了一个比担保更严重的消息,二公司在陕西的一个施工队,中午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,死四人伤六人,伤的六个人里,现在还有两人处于昏迷状态,也就是说随时有可能停止呼息,死亡数字悬在空中。
时代在更新,社会也在脱胎换骨,现在的企业当家人,不像早先的企业领导了,早先的企业领导有三怕,怕天怕地怕上级,而现在的企业当家人,虽说也有三怕,但内容大不一样了,称之为新三怕:一怕女人缠,二怕礼钱黑,三怕出事故死人。
人命关天,不是闹着玩的事,尤其是现在讲以人为本,一个企业里老是死人还怎么以人为本?如今企业里死人也有指标,而且是硬指标,与企业主要领导晋级、长工资、出国考察,以及企业评级、先进单位评选、劳模指标划拨、全员工资长浮等一系列利益挂着钩呢,一局物资公司年初着了一场大火,眨眼间就把一局全年的三个死亡指标烧光了,当时袁坤脖子粗脸红,气得要死,在事故现场指着物资公司一把手的鼻子说,我求求你了,你千万不能想不开了自杀,我现在可是没有死亡指标给你糟蹋了!从这以后,袁坤的心,就一直在安全生产上打转,就怕哪儿再死人,再死人一局就消化不了了,到时的一系列麻烦,可就不是钱能打发走的了。然而怕什么来什么,你越是不想见到的、听到的,偏偏就往你眼前挤,死活就往你耳朵眼里扎,这次车祸一下子就要去了四条人命!
有时人想悲哀,也得有资本垫着,也得凭底气撑着,袁坤现在已经没能力跟现实顶牛了,他说服自己冷静下来,然后让秘书通知在家的班子成员,马上到小会议室开紧急会议。
参加会议的领导,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里,袁坤也没什么开场白,直接通报了陕西事故。
常务副局长愁眉不展地说,这次事故来的真不是时候,这不是往二局踢那两个亿嘛!
袁坤挥挥手说,说眼前事,说眼前事。
其他领导不知说什么好,唉声叹气。
袁坤点着一支烟说,我们没时间发牢骚,也没工夫痛苦,大家还是抓紧时间,商量一下成立事故调查小组和相关善后处理事宜吧。
议了不长时间,事故调查小组就成立了,牵扯相关部室领导六人,常务副局长任组长,连夜奔陕西,同时兼顾善后处理事宜。
袁坤无可奈何地说,北京方面,我亲自去请罪,老天爷要灭一局,我袁坤也是束手无策啊!
工会**一听他这番泄气话,立马就酸了鼻子,动情地说,袁局长,我陪你进京吧。
袁坤摆摆手说,算了**,这要是进京领奖送温暖什么的,我倒是可以考虑带上你,去受罪就免了吧。
常务副局长说,袁局长,那我们这就准备出发了。
袁坤起身道,路上加小心,到了那里也别着急上火,事情已经这样了,尽量往好上办,你们也就尽力了。记住,安全安全,随时联系我。
常务副局长说,好的袁局长,那你也保重。
行了行了,袁坤苦笑道,都快忙去吧,怎么弄出了生死离别的味道,我可是等着你们平平安安回来呢。
回到办公室,袁坤左思右想也没敢给苏南和温朴打电话,但这事按规定又不能下压,必须在第一时间上报到部里。
袁坤续上一根烟,清理了一下思路,把电话打到了部安全生产管理局,算是先报个到,详情等他进京汇报。
3
袁坤进家后草草了了把晚饭吃了,然后一声不响地进了书房。
小女儿给他送来茶水。
袁坤还有一个大女儿,正在武汉读研究生。他望着小女儿的脸,感觉她还没有摆脱今年高考落榜阴影的纠缠,孩子还在为失去的东西伤心难过,心里不由得打翻了五味瓶。
小女儿望着他,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,似乎有什么话要跟他说。
他这时也很想跟小女儿聊点什么,他意识到这些日子自己对小女儿的关心太少了,好像就没怎么与小女儿说过贴心挨肺的家常话。
他努力把心里的慈祥,笑到脸上来,揽过小女儿,摸着她的头说,看你这不开心的小模样,是不是还在想考学的事?想开点,也就是差几分嘛,还有明年呢。
小女儿低下头,咬了咬嘴唇说,爸,我就是运气不好,你看人家小菲,去年进了北京,今年考分比我低一块都一本录取了,有北京户口,沾多大便宜呀爸。
小菲是随父亲工作调动进京的,小菲父亲进京前是袁坤手下一个处长,小菲离开东升前是袁坤家的常客。
小女儿靠住他,抠着他的一个衣扣,可怜巴巴地说,爸,干脆你也找找人调北京去算了,你还是个局长呢,小菲她爸去北京哪会儿才是个处长。爸,我要是进了北京,明年保准能考进名牌大学。
小女儿的话,小匕首一样划过袁坤心尖,他心里一抽动,嗓子眼就堵了,像是那儿卡了一枚泡开的胖大海,涨乎乎地难受。他控制了一下情绪,目光重新落到小女儿脸上,这时小女儿湿眼睛里的委屈目光,让他的心再次动荡,他直想流泪。
小女儿读初中时,学习上的事,袁坤还不怎么操心,那时小女儿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排在前五名,谁知升入高中后,小女儿的青春骚动了,搞上了对象,心思一下子从学习上溜开了,后来班主任觉得再假装看不见就坏事了,只好找小女儿谈话。子弟中学归一局管,袁坤的小女儿,不论是在学习还是情感上,一旦出了差错,甭说班主任背不动扛不起,就是书记、校长也得吃不了兜着走。谈话不愉快,小女儿不拿班主任的劝告当爱护,还厌烦地对班主任说,我的未来用得着你操心吗?我就是考不上大学也能找份比你强一百倍的工作……班主任再委屈再生气也不敢发火,袁坤的小女儿就是一局的公主,哄她也许还轮不上你呢。可又怕以后担责任,班主任没辙了,只好亲自跑到袁坤办公室来汇报。
袁坤转天抽时间找小女儿谈了一次话。他很开明,并没有像一般家长那样嗷嗷发火,对学生谈恋爱不依不饶,他只是说高中时期谈恋爱,有可能影响日后的高考,而在中国,高考对一个学生的未来是很重要的,他让小女儿三思,自己把握未来命运,拿得起就拿,拿不起现在放下也来得及。
其实袁坤知道,小女儿之所以有资本早恋,不拿眼前的高中和未来的考大学当回事,都是因为她有一个当局长的老爸,晓得日后即使考不上大学,在老爸眼皮底下找份研究生,甚至是博士生也捞不到的好工作,那是不费吹灰之力,一局多大啊,可挑选的工作太多了。至于说出国学习这条路,他知道小女儿的盼头不大,要是可以随便出国上学,当初她姐姐就出去了。前些年领导落榜子女出国上学成风,老百姓看在眼里,恨在心头,骂在嘴上,一些眼里不揉砂子的人,还往部里写信反映情况,质问领导家哪来的那么多钱供子女出国上学,老百姓家的孩子怎么就没钱出去?出去那么几个,也是父母砸锅卖铁拼家底,差点了再去找七大姑八大姨献爱心。部里很重视这个问题,因为不光是东升这边的老百姓对领导子女出国上学牢骚满腹,其他地方的直属单位里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。很快,就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及子女出国旅游上学等问题,部里下发了一个相关的预审暂行规定,内容涉及境外院校名称、资金证明等一系列敏感问题,于是这两三年里领导子女基本没有出国上学的了,曾有一个处长玩假过户,把儿子送到了澳大利亚上学,结果是受到了党内和行政双重处分。
后来小女儿虽说没有终结自己的早恋,但拿学习也没有完全不当回事。
袁坤面对这样一种不痛不痒的现实,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顺其自然了,不在小女儿早恋这件事上饶舌了。
高考前夕,一天袁坤有应酬,大半夜才回来,见小女儿还在高考冲刺,瘦弱的上身,只有文胸拦着,而当时开着空调的房间里,大概只有十五六度,袁坤一进房间就感到了冷气袭人。他退出房间,去书房取来一件自己的外衣,蹑手蹑脚靠近小女儿,小女儿就在他差一两步走到身旁时知觉了。他把手里的外衣披到小女儿身上,说时间不早了,休息吧,要是累倒了,就没法高考了。
小女儿这时也是累到了极限,打着哈欠站起来,伸着懒腰说累死我了爸,我要去睡觉了。等小女儿走了以后,他意外发现小女儿的坐椅上红了一片,弯腰仔细一看,再抽鼻子闻闻,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这孩子居然都不知道自己来月经了,心里禁不住难受起来。转天早晨,他把小女儿来月经的事告诉了爱人,爱人一听就红了眼圈,说这不是在玩命嘛我的傻闺女……
你们当官的就是这样,个个自私!小女儿扭过身子,跺了几下脚,一脸怨恨地走了。
他木然地承受着这一切,之后回味着小女儿的话。
袁坤想,小女儿怨,伤亡职工家属骂大街,下岗待岗职工联名上告,三岗制步步受阻,技术人才不停地外流,施工机械设备等待更新,计划内工程眼见消失……家里家外的日子都没个亮闪,这种局面自己究竟还能支撑多久?唉,如果这时能去北京的话,也是挺好的一件事,在东升这块土地上,自己这张脸给人看着风风光光,飘飘洒洒,可是有谁知道自己每迈一步都吃力呢?而且是忙忙碌碌中也没把一局搞出个太平样来,事事总是累不到点子上。
哀哀之中,袁坤晃了晃脑袋,意识到一局的日子,马上就没法儿过了,乱套的那一天就是二局得到两个亿那一日,就算一局二局合并,想必自己也没好日子过。常言道,瘦驴难拉磨,跛脚马跑不出速度,瞎眼牛只能转熟场……
一直坐到夜深人静,一直到睁不开眼睛上床睡觉时,袁坤才打定主意,尽快进京面见苏南。
4
就在袁坤为陕西死人这件事不知怎么痛苦好的倒霉下午,白石光跟马义的账也算清了。
白石光是在下午五点多钟回到东升的,两脚落地后,他没急着回家,在一家小卖部使公用电话与赵松联系。他在山西和千文市时都给赵松打过电话,想跟他解释一下有关情况,表示一下歉意,可就是听不到赵松的声音,赵松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。
白石光拨通了经理办公室电话,接电话的人说赵经理下基层慰问还没回来。
白石光扣下电话,望着天空,琢磨着是不是应该给温朴打个电话,但他一时又拿不准温朴现在知不知道这件事?知道了又会知道多少?心里这么一推磨,就越发没底了,不得不打消了联络温朴的念头,觉得还是等自己把事情办到亮堂处再跟他打招呼好一些,因为有些话,现在怎么说,都没办法说明白。
证明我白石光是人是鬼,不在乎这么一点时间。他的上下牙咬出了声音。
交了话费,白石光到路口拦了一辆红色出租车。上车后,不等司机问他去哪儿,他就说去水务局。
出租车拐上嘉乐街时,白石光觉得脚底下有什么东西滚动,弯腰拾起来一看,是一大瓶雪碧,觉得气味不对,拧开盖子一闻,里面装的是汽油。
司机说,中午两个醉鬼带上车的,说是去放火烧移动大厦,你说这不是找病嘛,他俩下车时,我把瓶子唬弄下来了。
白石光哼哈地听着,忽然意识到这瓶汽油对自己很有用,就说,师傅,把这瓶油给我吧。我出差刚回来,这是去单位骑摩托车,我担心油箱里的油不多了。
司机说,只要不去放火烧移动大厦就行,拿去拿去。
白石光离开千文市前,跟大秋约好要他暂时对马义封口,所以马义现在还不知道白石光身上掖着三百万的汇款。但马义一见白石光,还是觉出了不妙,目光直往门口溜。
白石光把马义逼到老板椅上,陶出汇票,在他眼前晃着说,三百万,我全带回来了。
马义想站起来,被白石光按了下去。
白石光把汇票装进手包,然后把手包扔到沙发上,掏出打火机,拧开雪碧盖子,二话不说,顺着马义的脑袋瓜子浇下去。
马义给浇傻了,等反应过来时,白石光已经住了手,他只浇了半瓶。
马义抖着嘴唇道,好兄弟,我错了,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行不?
白石光骂道,王八蛋,你够毒的了,你知道被人坑被人骗是什么滋味吗?我上有老下有小,你也下得了手?说到这两眼潮湿,把剩下的半瓶汽油倒到自己身上,又说,那好,老子今天就找你这个杂种陪死!
马义瘫了,拱起手说,别别别,开个价怎么样?
白石光伸出裹着绷带的断指说,不见的那半截,我送给大秋了,你说这个价怎么开?
马义的身子,又矮下一截,绝望地说,十万!
白石光摇摇头。
马义又说,十五万?
白石光笑了。
马义往起挺挺说,十六万!
白石光看看手中的打火机。
马义闭上眼睛说,十八万!
白石光这时产生了错觉,越看马义的脑袋,越像一个卡通大鸭头,这错觉让他从记忆里勾出了成片成片的野鸭子,洼子淀里的野鸭子,还仿佛看见一个长得跟白石光一模一样的青年,趴在船边,一张麻木的脸上,鲜血淋淋,正在机械地咬着野鸭子头,咔嚓咔嚓……
马义看到白石光的脸色越来越狰狞,身子就不住地筛糠。
白石光说,十八万,这个数,你就心疼了?
二十万!马义咬牙说。
白石光顶上说,你要是我呢?这个数,满意不满意?
二十……一……二万……马义的舌头打颤了。
白石光挺直了腰说,我操你妈,甭费口舌,二十五万,少一分你死定了!
马义梗直脖子,把一只在桌底下攥紧的拳头摆上了桌面,从嗓子眼爬出两个字,行吧……
白石光说,在这个一言为定上,你小子还可以再骗我,但你最好先把全国的汽车都买到手。
马义望着白石光,不知是因为内疚还是惜钱,竟然掉下了成串的眼泪。